一篇读懂(唐山知青诗社 总25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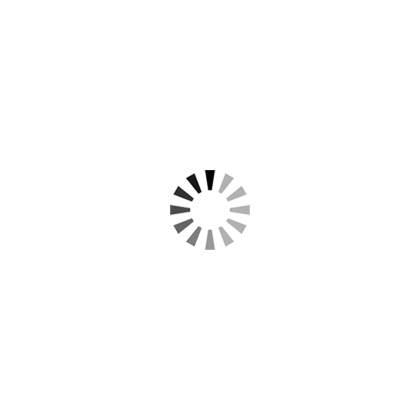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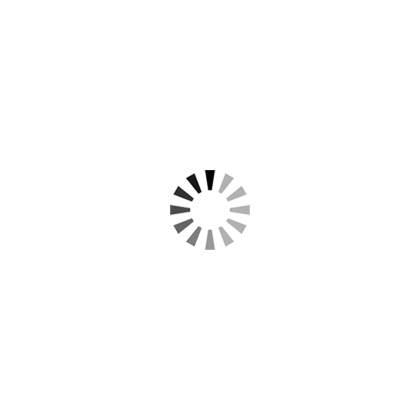
在抗日烽火中的父亲
文/文阁
近日好友郑文忠筹办《抗日烽火在冀东燃烧》摄影展,不时发来照片及进展情况。他们已在北京抗日纪念馆成功开展,轰动京城,首都二十多家媒体争相报道,首日参观人数达八千。纪念抗战是国人的一个永恒主题,今年八月十五我们将迎来抗战胜利七十三周年。我不由得想起父亲断断续续给我讲过的,他在抗战中的一些经历。父亲生于1911年,1937年抗战爆发,他应该是二十六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我们老家在栗园乡曹家庄,也成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政权——农民抗日协会,简称农会。父亲有一定文化,能写会算,负责管理农会帐务,筹粮筹款,给抗日武装号房派饭,接待路过的抗日武装等事宜都是他操办。他在庄里人缘好,又有工作能力,虽不是领导,但做了大部分工作。我小时候他跟我说,“我还接待过节振国的抗日队伍,是夜间来的”。那时抗日队伍都是夜间活动,农会人员就在夜里鸦没鹊静地通知有关人员,做好各项工作。1938年,冀东爆发了抗日大暴动,当时号称十万人。也影响到我家乡一带,离我家三里地马庄子的蒋林江,较早接触到党组织,他成为了暴动骨干,曾拉起过上千人的队伍,人称蒋司令。父亲与他有过交往,解放后蒋林江改称林江,是抗战时期老干部。林江后曾任烈士陵园园长,与父亲工作地点很近(蔬菜公司陵园菜窖),老哥俩经常在一块唠嗑。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大概是1940年以后,日寇加强了对抗日武装清剿,扫荡。一天蒋林江跑到我家,说日本和伪军正追他,他身上背杆大枪,父亲给他一件大褂,让他把枪夹在大褂里从北门跑出去。随后父亲也抄起一个粪箕子跑了出去(粪箕子做掩护用)。他们刚跑不远,追赶的伪军就到了。在院子里,屋里到处搜,还朝北门打了一枪。家中只有奶奶,婶子们,伪军们对奶奶说,“你儿子在农会,跑那去了!”奶奶说不知道,一个伪军拿起一把条帚,点着了,在屋乱舞说要烧房,并把屋内的一幅画点着了,奶奶拼命夺下,伪军就给奶奶一枪托子,脑门顿时鼓起个包。四婶见状,忙从桌子底下拿了一瓢鸡蛋,说好话,央告他们,这才罢休。父亲管农会的帐,也兼管钱,有时要给农会、抗日政权买些东西。有一次他们去唐山市里买东西(油印机和纸属违禁品),在过老火车站的卡子时被扣住。我小时候,有一次父亲和我路过震前唐山十中西门时,父亲对我说,日本子就把我押到这来着。当时刑讯拷问,特别是过电刑,一通电浑身酸痛颤抖,小便都失禁。在2005年我曾写过一短文,发表在唐山电视报上,我讲的是日本的稽查机关,后经群友平德增考证是日本宪兵队和冀东伪政府王辑唐所在地。父亲被扣押后经村里、家人找人使钱给保出来,真是九死一生。我们庄是抗日政府第X区,对于父亲的工作,区长在大会上直接表扬,并有会编快板的人把父亲的工作和其他先进人物、事迹编成快板一起传唱。这也是父亲常引以为自豪的事。小时候父亲给我们讲这些事的时候,一向不苟言笑的他竟也唱起了抗日歌曲:“八路军好,八路军强,八路军打仗为老乡……”中国人民历经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这里有无数抗日英雄,抗日先烈的流血牺牲,也有万千像父亲一样有爱国情怀的普通百姓的参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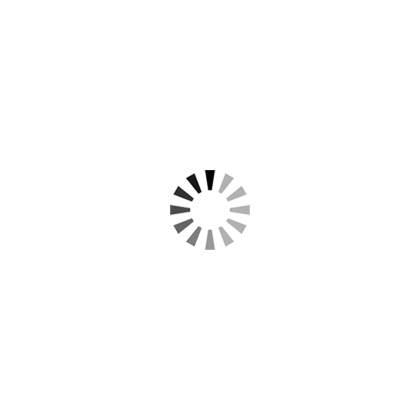
父亲的遗言,母亲的遗忘。
文/曹淑玫
父亲作了一次开颅术后,在恢复期内又摔倒了,引起大面积弥漫性颅内出血,经抢救无效,于2006年5月27日与世长辞。父亲的去世对我和母亲的打击都很大。父亲的遗言始终留在我心间,成了我陪伴母亲风烛残年的座右铭。“如果我先于你妈走一步,和你妈在一起,好好照顾她。” “明友(孩子他爸)地震中救了我们,要记住。无论发生什么变故都要尽量原谅他。他本质是善良的,和他一起好好过日子。”这是父亲生前对我不止一次说的。记得在我去参加一个研讨会的前一天晚上还说过这话,想不到这却是父亲昏迷前的最后遗言。父亲的话始终是我陪伴母亲,战胜生活中的各种不期而至的变故,适应各种环境,抑制自己情感的“放纵”,改变自我,自疗感情上的创伤,冲破重重枷锁,从低谷中反弹、崛起的一股强烈的冲击波。对于母亲而言,她的遗忘,小脑萎缩却是她摆脱失去与之相濡以沫的伴侣的哀痛的幸事。父亲刚去世的那段时间,每到吃饭她都在父亲坐过的位置前摆上碗筷,盛上饭,夹好菜,呆呆地看上一会儿,直到我催她几遍后,才慢慢端起饭碗吃上几口。我收拾完碗筷,她还要在父亲的座位旁,手扶着椅子站上一会儿。后来,母亲渐渐有了反常的举动和话语。她常常叫着父亲的名字“金岳,该起床了金岳该吃饭了,金岳咱们到街上溜达溜达去吧……”母亲的这些言行举止令我不安,但我知道任何劝慰都无济于她对父亲的思念。这也是传统思想对我的非同一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母亲渐渐地发展到近乎痴呆了,她忘记了父亲的去世,但更显现出对父亲的百般体贴和牵挂。她常常催我叫父亲吃饭,还常常埋怨父亲不回家,贪玩,只知打门球。有时还气愤地骂上几句”这死老头,真自私。整天不回来!”我很无奈。每当这时我都很难过。是因母亲的糊里糊涂吗?不是。是母亲对父亲的思念,也可以说是母亲对父亲的依恋和深情。到后来母亲时不时地把我当成她姐姐,妹妹甚至叫我“漂亮保姆”我知道母亲的头脑越发不清楚了,生活越来越不能自理了,大、小便常常失禁。但有一点她每当我给她净身的时候,她都把我当成外人千恩万谢。我说:“妈,千万别,这是应该的。我小时候你不是一样为我洗吗?现在该我为你洗了。”她说:“是吗?我怎么不记得?我真太拖累你了,谢谢你。”然后就哈哈地笑了。我想”忘掉一切”在某种程度上是件好事。只有远记忆,美好的回忆冲淡了近时的不幸和烦恼。偶尔记起令她不快的或伤心的事,也会短时逗留,瞬间即逝。老妈总是整天乐呵呵的,烦恼与她无缘。有这样乐观,豁达的老母亲陪伴够幸运的了,我爱老妈。如今二老都离我而去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始终留在我心中,愿他们在天堂快乐、幸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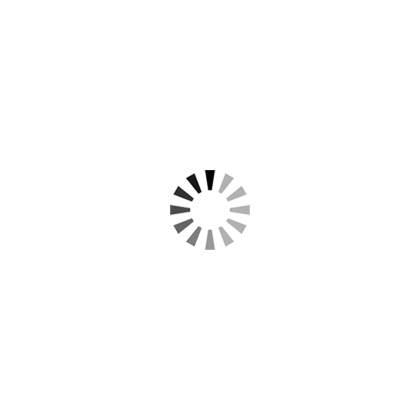
最后的诀别
文/王瑛
早上离开家的时候,妈看着我把毯子夹在自行车后座上,又用一根麻绳把毯子固定到后座两侧的立柱上,妈送我到门口,嘱咐我路上注意安全(以往妈并不嘱咐我,她以为小女儿独自一人持过家,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吧)。“放心吧,这条路我走了好多次了”(唐山到丰南大新庄的唐海路)我推着车子往院外走,妈跟着我走到院大门口,“路上注意汽车,靠边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妈从来不曾絮絮叨叨地嘱咐我们,妈似乎还是不放心)。“你回去吧,我骑上了啊”我偏腿跨上了那辆28自行车,唐山离大新庄黑坨村大概70多里地,按照预定计划中午前我还要赶到村里,前天回唐山时跟工作组的老吴说好了,今天中午给我号饭。这是1976年五月的一天,这次回家是把冬天的棉被拿回唐山换季,朦朦胧胧感到这次妈舍不得我回农村去了,可能因为我爸解放了,她自己也退休了。“小英等一会,小英……”,隐隐约约听到妈在后面拉长了声音在喊我,这声音听起来有点急迫,怎么了,有事吗?我在心里画了一个魂。跳下自行车,回头看到妈正小跑着追上来,准确地说这是记忆里第一次看到妈跑,妈的头发在跑动中微微地颤抖着,手里拿着什么?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等我20岁时,妈都55岁了,她一贯的性格是很内敛的,从来不急不躁,这是怎么了?妈擦了一下脑门上的汗,由于跑了一段路,妈的脸色微微泛出了红色,说话的声音有点急促:还是拿根行李绳把毯子再捆捆吧,妈抖落开手里的浅绿色扁平行李绳,看到妈是为这事追上来,我不以为然地说“没事的,捆得挺结实的”妈的声音有点颤抖:挺远的呢,还是再捆一下吧(之前爸妈去黑坨看过我一回)。我只好支起车梯子,每次我离开家都是二姐把物品整理好,我自己捆在车子上。我去拉妈手里的绳子,妈:你捆得太松,半路歪了不行的。妈弯着腰用力去拉紧绳子的背影让我感到有点心酸,她那染过的头发齐刷刷地长出了白发,我晃了晃那行李很稳当了,果然比我捆得结实(有一次妈说抗战时她们一夜走了80多里地到冀中分区去集训)。“我走了啊,你回去吧”,妈似乎还是不放心“我送你到柏油路上吧”。“没事的”,妈又跟着我穿过小树林到了柏油路上(小树林是凤凰路南端的一片绿地,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小树林中间有了一条小土路,柏油路是唐山市工人文化宫南门口到西山口黄大楼的一条柏油路)。不记得又说过什么话了,但是记得自从我下乡以来妈从来没有送过我,从来没有。她很放心独立性极强的小女儿。这次妈送我回丰南令我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让我说不出来的感觉,从来没有过的心念,这种感觉仿佛是一张看不见的网纠缠在我的身上,非常莫名其妙的感觉。妈反复地提醒我注意安全。似乎要把一生的嘱咐都凝聚在这条短短的路上,妈反复地延长我们分手的时间,她似乎知道这是最后的诀别。其实,这最后的诀别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终于这种感觉把我带到了妈妈失去生命信号的家、一片瓦砾、一片废墟,一个孤独的女孩坐在废墟上嚎啕大哭……自唐山的7.28地震以后我很相信直觉,时常为了直觉取消一个活动,为了直觉坚持做一件事情,为了直觉甚至于改变过自己内心既定的方向。2022.11.13写于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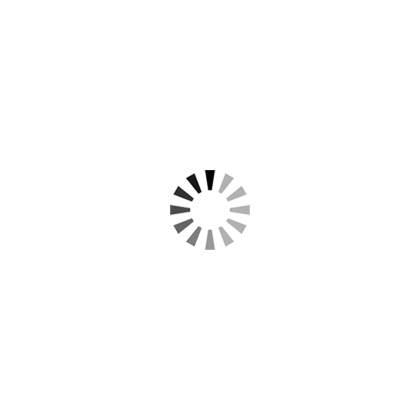
珍贵的纪念
文/空空大士
这是一本1971年修订、扉页印有毛主席语录、文革时期为方便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专门发行的一版商务印书馆出版、定价1块钱的《新华字典》。说起这本字典,还有一段我和父亲间的小秘密,从未向第三人透露,就连我最亲的妈都不知道。1970年10月,我初中毕业,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丰南西河插队落户,成了我家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下乡知青。每次回唐山,总是和一帮小伙伴泡在一起,晚上很晚才回来。早上父亲上班时我还沉浸在梦乡,他又舍不得叫醒我,爷俩说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回家十几天,和父亲基本上见不到面。那年我16岁,年轻单纯,对老人家地牵挂根本就没有概念。1972年秋天,妈妈悄悄告诫我,爸爸多次抱怨我,从乡下回来,天天不着家,面都见不上一回。那天晚上,我哪儿也没去,就呆在家里陪爸爸聊天,这个从不显露温情的男人显得非常高兴。爸爸1928年生人,16岁从老家到唐山,在买卖家学徒,1950年入职花纱布公司。老人家上过村里的完小,酷爱唐诗宋词,对历史、典故也如数家珍。也不记得爷俩怎么就说起‘各有特点’的话题,我形容说:燕瘦鸭肥,各尽其美。爸爸沉吟良久,给我讲起杨玉环、赵飞燕的故事,最后跟我说,从字面上看燕瘦鸭肥,客观上也没错,可是美就不见得了。这成语是有典故的,赵飞燕的轻盈,杨玉环的华贵,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倾国倾城,才留下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燕瘦环肥,各尽其美”感叹。遗憾的是,先天不足的我已经“鸭肥”好多年了,还曾多次在人前卖弄,想想就汗颜不已。第二天爸爸下班回来,没有赠言,没有寄语,默默递给我这本《新华字典》。自从有了这本字典,凡有疑惑之字词,必当虚心请教“老师”,记取了“鸭肥”之教训,绝不似是而非。久而久之,掌握了大量的汉语词汇和汉字的正确读音,别人不认识的字,我认识。别人不懂的词我懂,渐渐被身边的朋友尊称“活字典”,有问题都喜欢来问我。寒来暑往,岁月如梭,50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这本字典跟我上山下乡、陪我地质勘探,最远曾跟我到过海南岛。如今,字典原来的面目已经全然不见,斑驳残破见证着和我风雨人生的起起落落。字典原来是褐色的塑料皮,中上部四个宋体阴文“新华字典”。不烫金,不描红,素雅庄重,曾经让我爱不释手,要知道,那个年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本新字典的。随着岁月的侵蚀,塑料皮逐渐老化碎裂,前面硬纸插页和扉页部分也与字典本体脱离。父亲的礼物本就珍爱,况且,我也离不开它。用我的一方蓝色男用大手帕,巧借其原有的浅色长条图案,精心裁剪、裱糊,装帧成了一本独一无二的布面精装版《新华字典》。在正面浅色条框中间工工正正写下“新华字典”四个毛笔字,乍一看浑然天成。看着焕然一新的字典,还真让我骄傲了一阵子。不管是插队落户的乡村土炕还是海南三亚的育种基地,不管是野外勘探山间的帐篷还是机关静谧的办公室,哪怕是出差在外的路上。不论生活环境发生什么样改变,这本字典一直都是我随身必备,即便是智能手机包揽一切的今天,这本饱含着老父亲殷切希望的字典依然摆放在我的案头。布面的装裱也难逃岁月的磨难,还是原来的破损之处,我却不舍再动手修补了,只在字典内页抹点胶水,粘贴起来。就在写下本篇文字之前,轻轻翻检这本字典时意外惊喜,在《化学元素周期表》后泛黄发硬的内页左下角发现两个隽秀挺拔的钢笔字“玉峰1972.3.31”, 原来这是父亲自用的、刚买了半年的《新华字典》,由于我的“燕瘦鸭肥”而割爱,而我用了50年竟浑然不知。此时,老父亲的亲笔,比任何寄语、赠言都更深沉、更宝贵。1990年11月29日清晨,卧床病榻半年之久的老父亲,看着我的《公务员录取报到通知书》,欣慰的含笑而去,放下对我的无边牵挂,走完他平淡、多舛的人生。这本经风历雨的《新华字典》以及“燕瘦鸭肥”这个典故中的典故,也成为父亲留给我最珍贵的纪念。孙来幸
电话:17736585884
地址:兴源里协通阁1-402
2020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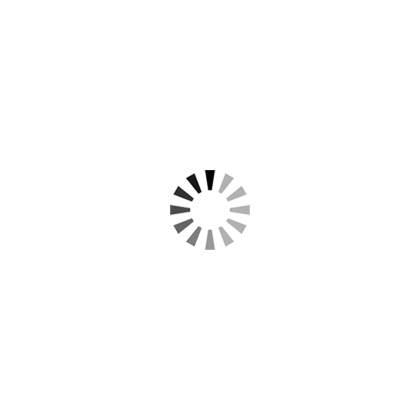
差点走失的妈妈
文/王秋华
那是1997年6月份的一天,我和镶复科的郑大夫约好,要带我71岁的老妈去镶牙。上午9点钟妈妈坐5路公交车到了我的办公室。我把妈妈送到镶复科郑大夫那儿。郑大夫说:“大姐,你就上你的班吧,待阿姨咬好了牙印,我给您打电话。”我连声说:“好,好!”11点左右我接到郑大夫的电话后,将妈妈送到了站点等公交车,十来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来车。我的心情有些急躁,因为我是护士长,平常工作很忙的。妈妈理解我的工作性质,就说:“上班时间你回医院吧,我知道做5路车到体育场站下车就到家了。”我也知道上班时不能耽误太长的时间,就把妈妈放在公交车站点回去工作了。中午下班我回到自己家中,吃完饭正准备睡午觉,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我开了门,老弟弟心急火燎地说:“妈在没在你家?现在都一点半了妈还没到家呢。”我急得马上骑自行车和老弟弟分头去找妈,快两点再次找到妈妈家,见她坐在餐桌前正在吃饭,我和老弟弟悬着的心才落下了。我埋怨妈妈催我回去上班,结果出事了吧?妈妈就像犯了错的孩子样一声不吭,爸爸此前急得连眼睛都哭红了(可见老两口的感情之深)。老弟弟又把矛头对准了我,说:姐当时给我打电话,我去医院接妈妈就没事了。我也直后悔做事不周到,欠考虑。在我们的再三追问下,妈妈说出了缘由,当时是坐错车了,把18路当5路坐到冯大里(路线不对)才发现,急忙下车后一边打听一边走回家。细想起来路程也有七、八里地吧。我们问她咋不打的回家?她幽默地说我看牙带100块钱怕打的司机找不开,走回家就当锻炼身体了!其实她就是一辈子节俭舍不得花钱。这时家里的每个人都笑了,差点走失的妈妈回来了,咋不令人高兴呢!现在想起此事,犹如发生在眼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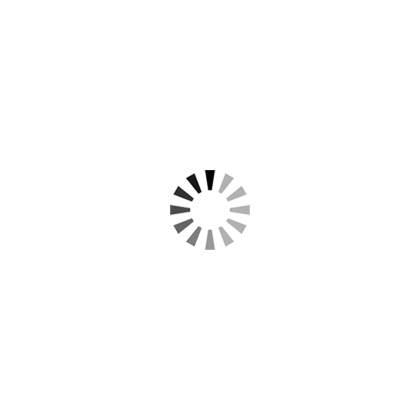
赶海
文/志农
壬寅菊月二十,闲来无事,十一长假时带珠珠捉的小海蟹不知什么原因接连都失去了生命,玻璃缸空着,仅剩下给小海做窝的几只贝壳,就想去海边再捉些小蟹来养,小海蟹是孙子珠珠的宠物,最长时间可以活小一年,他的同学们谁都没有。
说走就走,妻驾驶驱车百里到了曹妃甸海边,停好车,来到一号路跨海桥西侧那段用石块和建筑弃物填起的海岸,我们过往经常在这里手到擒来捉过很多小海蟹还捉过几只八爪鱼。
我还在穿胶鞋套,妻早就开始翻动粘满牡蛎和滕壶的石块了,一会儿,听妻喊:“今天好象涨潮没有螃蟹,这儿有个小螃蟹,要不要?!”,”不要!”“那扔了”。
穿好鞋套,我也开始翻动那些下面可能藏着小螃蟹的石块,可是翻了好多,真是一个小蟹也没见到,只有一群一群的海潮虫子四散逃跑,偶尔有几条海蚯蚓,但就连黄豆大的小蟹也没有发现一只。
看着海水不见退去,“是不是涨潮呢?”妻问,我看了看半浸半露的可参照石块,海水一波一波湧动着也看不准,只得说“等等吧”。妻说:“那我查查涨潮退潮”拿出手机,翻找,念到:“2022-10-15.农历九月二十,星期四,涨潮从四点几十至十一点几十,退潮十一点几十至…”。
原来今天不逢时赶上涨潮,那也不甘心,我又卖力地翻起石头,终于,当我搬起一块大石头的时侯,在石头窝里发现仅有一只衬衣纽扣般的小花螃蟹,赶紧仔细把它捉起放进灌上海水的矿泉水瓶中,若是在往常这么丁点儿的小蟹多得都数不清,我是决不会要的,可今天不同,到现在也只捉了这么一只。不甘心,又继续搬石块翻找,但仍再无收获。海水仍一点儿一点儿地还在涨。我和妻商量:“先去别处转转,然后吃饭,吃完饭再来。”
驱车过二号路跨海桥来到南岸工业厂区,向西道路尽头一块吹海造出来的贝壳沙荒地上有片片鲜红盐蒿映衬着荒芜的干草;掉头东行来到一处海湾,向北岸望去可以看到曹妃区管委会大楼、四海小镇,眼前大约百十米一个小湾有几只渔船泊在岸边,这时从远处一号路桥方向开来一叶小艇,速度很快,在清澈的海面划出了优美线条后一个点刹潇洒地靠上一艘渔船,渔船中下来一个人登上小艇开往我们驻足的坡岸,和等侯在岸边手里拎着一袋蔬菜的人做了交换,小艇又返回了那艘渔船,看来是接送补给的。
沿南岸路继续东行,到了一座摆滿渔杆的桥上,有很多人在桥两侧的海湾里钓鱼,其中一个水桶里盛着七八条长着斑点的鲈鱼,大的有尺把长。钓者多用甩杆钓鱼;还有钓者在桥面上的雨水管中垂线而钓,雨水管直径只有十多厘米,下面就是海水,很有趣。
看看时间十一点多了,赶紧找饭店吃饭。吃过饭立即回去继续捉螃蟹,到海边一看参照物,海水比上午走时还要高,心立时有些凉。
那也不甘,忙着动手翻找,努力有半小时,终于,妻喊到:"有一个小螃蟹!″“逮住!赶紧的!”我也喊到。
又翻找半天,愣是没有新发现,海水也没见落下去多少,顿时没了信心,看来今天就这样,决定返唐。
虽然一人仅捉了一只小到不愿意要的小蟹,这是赶海无数次收获最少的一次,但总算有收获没空手而归。
而且,身处渤海湾放眼广阔无边蔚蓝如碧的大海,看到昔日的海湾滩涂如今高楼林立,艎艆繁忙,心情是既愉快又忻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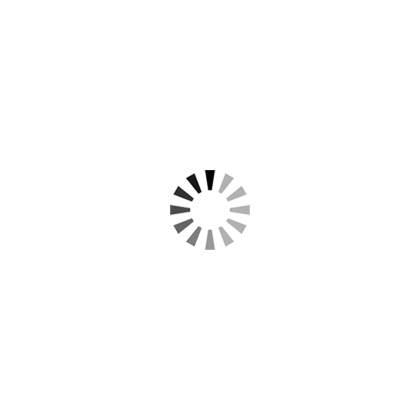
打听
文/李维德
熟人见面,或短或长,总要聊聊天儿。寒暄,问候近况,介绍近来所见所闻,内容很丰富的。有时还不忘打听一些共同关心的人和事儿,尤其是双方都熟识的、年龄相近的“同龄人”的近况。对于一些共同的熟人,都打听(关注)他们什么呢?真巧,前不久我和一位同龄朋友竟专门聊起这个话题。小时候,小伙伴们见面,打听谁谁考到哪所学校上学去了?再大些,打听谁谁毕业了吗?分配到哪(工作)去了?又过些年,打听谁谁结婚了吗?提拔了吗?提到哪儿(什么岗位任职)去啦?再过一段时间,打听谁谁有孩子了吗?后来:谁谁的孩子多大啦?再后来:谁谁的孩子该高考了吧?接下来,就打听谁谁的孩子是否大学毕业、是否结婚和出国了。到了接近退休年龄,就打听谁谁是否退休了?再往后,就打听谁谁的退休生活如何,有无孙辈,是否带孙辈及其老伴儿的身体情况啦。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已是逾耋年而奔耄龄的人啦。现在,每一次见面都感到非常亲切了。关注点也已从关心天下大事更多地转移到日常生活和养老方面来了。打听他人,更多地是打听谁谁的身体状况,饮食起居是否还正常,是否在住医院等。有时竟直白地问询“谁谁还有吗?”当听到“还健在”“不咋好,出来进去的都费劲啦”“不在了”等不同回答时,交谈双方都会自然流露出或欣慰、或同情与痛惜的表情。深感自己也在变老。从打听第三者内容的演变,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一代人的生活轨迹。庆幸的是,健在的我们40后50后这一代人,年龄恰好与当下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相近。企盼着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跟上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增长的步伐,老同事老朋友还能经常见见面,聊聊天,打听打听同龄唐山知青诗社启事
1. 《唐山知青诗社》微刊不仅是知青文化的一个平台,同时也是面向社会的一个公众号。欢迎国内外诗词爱好者投稿。
2. 本微刊共设二个栏目《诗意满庭芳》 《百味人生》。
3.《诗意满庭芳》周六发刊,内容为:诗词歌赋(含现代诗)、近体诗。投稿作品必须符合格律要求。
《百味人生》周三发刊,内容如下:
(1)散文、记事或回忆文章。
(2)对传统文化有较深的领会心得及学习经验等,要求言简意赅。
(3)诗词讨论文稿或诗评文章。
文稿字数限制1000字以内,文责自负。
4. 社会作者投稿邮箱:394383870@qq.com
5. 个人专辑投稿要求首发原创,投稿时附100字以内的个人简介和本人近期照片一张。
6. 所有投稿10天内本平台未录用可另投他处,本平台不另行通知。
7. 投稿必须原创,作者文责自负,本平台不负责版权纠纷。
8. 投稿作者敬请关注本平台公众号,并积极转发。
9. 本公众号纯属作品交流,非赢利性运营。
组 织 机 构
特 邀 顾 问:郭旺周 卜祥城
社 长:王 瑛
主 编:张树生
副主编:笑 盈 薛鹤舞 孙青燕
微信群投稿:唐山知青诗社
投稿邮箱:394383870@qq.com
往期经典回顾
◆
◆
◆
◆
◆
◆
◆
本文链接:https://www.yangzhibaike.com/post/30839.html
声明:本站文章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请发表您的评论